记得年前有个新闻,说金庸、徐志摩、琼瑶、穆旦、钱学森、沈钧儒等等都是亲戚,他们全家都是亲戚。我一开始不相信,因为每隔一阵子就会有类似的无聊文章,恨不能把民国名流..
刘禾感叹:与纳博科夫几乎同时入校,为什么徐志摩看到的那样少?或许不是徐的问题,是因为中国人很难进入白人的圈子。无论如何,徐志摩错过了多少精彩的人类精神戏剧,足够刘禾写一本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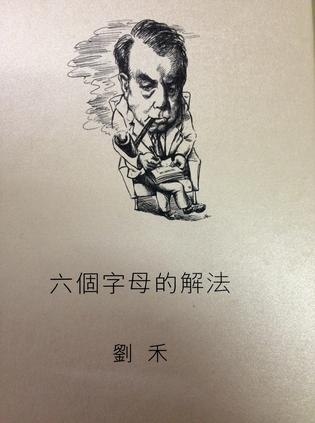
《六个字母的解法》
刘禾著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2013年10月第一版
记得年前有个新闻,说金庸、徐志摩、琼瑶、穆旦、钱学森、沈钧儒等等都是亲戚,他们全家都是亲戚。我一开始不相信,因为每隔一阵子就会有类似的无聊文章,恨不能把民国名流全都拴一根绳子上去。比如有个流行段子这样说:“林则徐有个女婿叫左宗棠,他有个连襟叫曾国藩,曾国藩有个儿子叫曾纪鸿,他的女婿叫梁启超。梁启超生了个儿子叫梁思成,梁思成娶了个老婆叫林徽因,有个单恋林徽因的人叫徐志摩,曾国藩女儿嫁给了宰相陈宝箴,抱了个孙子叫陈寅恪。陈寅恪的儿子过继给了曾国藩的曾孙女,生了个娃叫叶剑英。叶剑英的舅舅认了个演员干女儿叫蓝平……曾国藩的曾孙女的儿子叫蒋经国,他爸叫蒋中正……”
看,简直像在给纯种黑背取名,血统纯正,铺天盖地,而且里面总有个徐志摩,很有点萨摩耶的感觉。我一直对这种杜撰感到不舒服,想了半天才明白不舒服在哪里,因为这种段子把杰出人物和名流名媛混在一起等量齐观,只剩下势利。
段子归段子,就那个时代来说,因为能上学的人少,名流圈也就很小,所以名人之间确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有各种明媒正娶,还有各种奸情以及柏拉图式的奸情。金岳霖和林徽因、梁思成不是亲戚胜似亲戚,至今仍是一段文人佳话。
二十世纪初的名流圈真小,在英国也一样。
徐志摩同志本来是可以把中英两国名流圈联系在一起的。话说1921年他二十四岁,因为林长民的引介进了“康桥”大学,一只脚已经踏进英伦的高智朋友圈,也就是剑桥牛津两校的精英江湖。那时节,研究基因研究粒子的,思考中国科学史的,写下洛丽塔勾引日记的,还有一大堆后来拿了各种诺贝尔奖的,他们都在一个学校的老房子里学习生活争吵,天天擦肩而过,是是非非恩恩怨怨一大堆。可是徐志摩呢,腼腆鲜嫩,跟一朵雪花似的,“飞扬,飞扬,飞扬,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在康河边顾影辗转,导游一样,两年过去了,轻飘飘不带走一片云彩,当然也没有认识一个好基友。
这事我是看了刘禾的小说《六个字母的解法》才知道的。刘禾感叹:与纳博科夫几乎同时入校,为什么徐志摩看到的那样少?或许不是徐的问题,是因为中国人很难进入白人的圈子。无论如何,徐志摩错过了多少精彩的人类精神戏剧,足够刘禾写一本书。
这可是我第一本完整阅读完的刘禾作品。《跨语际实践》《帝国的话语政治》等学术著作当年令人耳目一新,触动到我,我却没有功力全部吸纳。可是现在她突然写了一部小说——也不是小说——想要告诉我们什么?
故事从研究纳博科夫开始。“我”感到好奇,为什么纳博科夫那么有钱却一辈子只租房不买房?在弄清楚这个问题之前又被另一个问题吸引住了——纳博科夫作品里的奈斯比特(NESBIT)先生是谁?这位在英伦家喻户晓,拥护列宁和十月革命,喜爱拿着烟斗和纳博科夫谈文学的左派人士,纳博科夫不愿意透露他的真名。纳博科夫流亡英国的时候在剑桥读书,有很多才高八斗的校友来找他聊天。奈斯比特一定就在其中,到底是谁?
为了完成这个拆字游戏,作者在各种图书材料里查阅,致信各种学者、知情者询问。小说一开始,她就为此去瑞士参加原本已经厌倦的学术会议。在火车上,竟遇到一个也叫奈斯比特的乘客。这是不是作者布下的一个叙述圈套?我不由警觉起来。这六个字母的字谜,以及文字间不时出现的“小径”、“小路”,都让我一度以为作者营造的叙述迷宫来了。我准备会心一笑:“圈套,你好!圈套,再见!”再没有兴趣像1980年代的知识青年那样接招,比如小说家马原在作品里布下了叙述圈套,评论家吴亮就表示:我要用不相上下的方式来批评你,我会比你的叙述更加圈套。如今,思想解放的圈套绕了三十多年,殷洪乔早已无心再做送书邮。
可是看到后来我放心了,没有迷宫,只有迷宫修辞的余风。作者志不在此,但也没有像她的学术作品那样富有雄心。说智者走下圣山有点夸张,说浮士德走出书斋也轮不上,作者好像是从象牙塔开小差。后记里说:“我有些不甘心,能不能在象牙塔之外做一点事?能不能为学界之外的读者写些什么?”之前的学术写作遁形了,帝国话语破解之战并未延续到这里。1919年,这个风暴间隙暗流涌动的年份高悬在故事里,昭示着作品的历史感。韩少功作的序言着重解读本书的微言大义和沉重命题。据说还有学者看出更残酷的革命隐喻。我没怎么感觉出来,我看见的是一个大约可以和纳博科夫、奥威尔、贝尔纳等坐在一起聊天的女士,当然也看见她怀着一些殷切的愿望——
整个故事像一段寻访,寻访那段本以为熟悉的岁月,重新思考“现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和“二十世纪蹉跎岁月”。寻找奈斯比特,这个课题不用申报,不用注释,不用答辩。瑞士、巴黎、伦敦……一路旅行需要的是随机应变。进出很多图书馆,寻访很多人很多房间,因为犹豫错过小镇蒙特勒便一再遗憾——“一个人在路上稍不留意,就会自动地被某个既定的目的地所约束”,两年后还是去了。为了看一眼纳博科夫住过的房间,她对前台小姐借口说要订房间。有点像昆德拉《不朽》里的阿涅丝,终于离开大道,旁支斜出。
1919年的景象清晰起来,或者说是谜团显示出来了。纳博科夫为什么要住酒店已经显然,但奈斯比特究竟是谁?会是李约瑟吗?会是贝尔纳吗?会是沃丁顿吗?不管是谁,这一路上发现那么多事情,遭遇那么多历史人物。他们活着的时候,与他们在后人眼中的假想形象相去甚远。为什么徐志摩看到的那样少?这个问题或许算是对今日附庸风雅者的暗讽吧?
艾略特、乔伊斯、梁启超……一个个已经化作历史标本的人物转过身来。我真想吼一声:“原来你也在这里!”连哈耶克都露了个头。对于不同政治立场的这些人物,作品里没有做什么褒贬。在学术世界一直以天下为己任的刘禾,现在可以放开索绪尔、福柯、马克思……放开当代文化政治的核心问题,把笔墨给那些自己生命中的人物和牵挂。比如毕加索的蓝色时期,比如在二十一世纪还被美国法律、保守势力迫害致死的伯克利“光身”小伙,还有本雅明的可叹之死。说到贝尔纳,原来其子小贝尔纳就是《黑色雅典娜》的作者,恰好不久前我刚刚编发过陈丹丹写的相关书评。忽然感觉那些燃烧生命的过去人物,冥冥中穿透时空给我们传递来一些启示。历史的朋友圈真小,原来你们都在一起。对此,作者没有像民国粉那样惊叹、赞美,只是走进他们的房间若有所思。叙述及其平静内敛。
称这部小说有思想领域侦探小说的味道当然没错,但我觉得这样评价可能损失了小说的另一番趣味——类似微信朋友圈的活生生味道。一个又一个圈子交集,中间乔治·奥威尔倒是扮演了真格的知识分子侦探角色。奈斯比特是谁,刘禾最重要的侦破线索居然是奥威尔交给英国情报调查处的一份“黑名单”以及奥威尔自己笔记本上的名单。
奥威尔是继徐志摩之后,第二个在这部作品里暗淡下去的人物。他早年参加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加入社会主义政党,还流浪巴黎伦敦街头体会穷人生活。最终却因为反苏反斯大林,同意与英国情报部门合作,提供知识分子的信息。他在笔记本上记了一百三十五个人,谁是共产党,谁是共产党同情者,谁是犹太人都一一标明,卓别林、萧伯纳等左翼人士都上了榜。刘禾没有上纲上线责难奥威尔,却根据这份名单去找奈斯比特,这真是比责难还厉害。说实话,奥威尔干了这么多活真是出乎我的意料。我能理解奥威尔,他是少见的有江湖滚爬经验的知识分子,朋友圈广,走过的桥多,甚至和中国的萧乾还有一段小龃龉。英国政府情报部门可能比我们想的要笨,搞不清知识分子啥情况,好比我国的《人民日报》大概到现在也搞不清楚公知、五毛、新左、小右到底怎么分别,就找奥威尔帮忙。奥威尔画了一张知识分子地图,比如某某某极端反美、具有强烈的同情品质等等。我觉得他要是来我们公司做客户资料整理和维护工作肯定是一把好手。说真的,被记录的左翼知识分子也不必惧怕什么,那个时候他们本来就不是地下党,光明正大。
做学问的人都知道,收集名人八卦真是一件远比写论文愉快的事情。刘禾在小说第十一章忍不住说这篇作品不很像散文不很像随笔不很像小说不很像传记,我觉得刘禾不说出来更好。这个由二十世纪国际知识分子掌故组成的故事,让我忽地想起《当世界年轻的时候》这本书。倪慧如与邹宁远这对出身台湾的自然科学教授,意外发现曾经有中国无名志愿者参加西班牙反法西斯内战,于是千辛万苦满世界找线索,终于让这些志愿者的音容笑貌重见天日。不知道这些志愿者在西班牙曾和奥威尔、海明威、爱伦堡擦肩而过没有?想必是有的,曾经有过一个超级朋友圈,一个人民的朋友圈。
相比小说家在写作时往往要拼命显示自己的学问以免被人看作没文化,由学者来写一部文学作品就有一大优点:她不会用上浑身解数,反而要隐藏她的学养,以免满纸术语隔绝群众。即使谈到历史学实证研究的时候,刘禾也只是弱弱地说:“最近听说,有人研究气候变化与人类战争的关系,拿出了大量的数据,声称战争爆发的时间和持续的时间,竟与气候变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之类。可惜刘禾毕竟谦谦女君子,对基情不太有感觉,不然写这么多极品男人理应更热烈一点。
故事从研究纳博科夫开始,但写作是从对学术生活的怀疑开始。这不是否定学术,倒像是冯象对法学人的期望——尚有正义感的法学院学生应该采取铁扇公主的战术,钻进律师行,悄悄破坏“魔鬼般反社会”的律师从业实践。人文学者能为现实做点什么?文学界标榜的无用之用真的有用吗?优秀的文学文化研究者是否也应该尝试发起夜袭?《六个字母的解法》是否想以“速朽”的方式,开启无声的功业?

![8[0000-00-00 00:00:00]Š 8[0000-00-00 00:00:00]Š](/Upload/1488543337.jpg)
![导航上面VIP广告[2017-03-03 19:53:54]
导航上面VIP广告[2017-03-03 19:53:54]](/Upload/1491552790.gi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