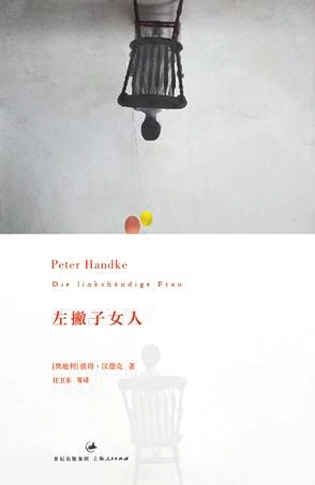
《左撇子女人》
作者:(奥地利)彼得·汉德克
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8月
□书评人 陆屿
彼得·汉德克书中的人物具有一种漫游者的气质,无论旅行、走动还是坐在屋子里,他们时不时地会走走神儿,犹如梦游症患者,虽行走于青天白日之下依然如在梦中,想象充当了他们的分身,让他们可以暂别刻板的生活,借由幻想和旁观反思自身的现实处境。但是,这也让真实与虚幻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他们自己也因此身陷困惑。读《左撇子女人》中的三部小说,这种感受无时不在,尽管人物的身份有所差别,而从本质上讲,他们似乎又是同一类人。他们看似平和,内心的风暴却强烈无比,不管是被动还是主动,是虚构或是真实,总之,一个突然事件让原本平静的生活突然发生了断裂,他们也就沿着那个豁口走上另一段路途。
变化出于“对日常生活规定性的厌倦”
说起来书中的主人公过得都很安逸,但表面的波澜不惊不等于没有凶险和不安,即便那可能只发生于想象之中。《短信长别》里的“我”是一个编剧,面临即将解体的婚姻;《真实感受的时刻》中的科士尼格作为奥地利驻法国使馆的媒体官员,与妻女过着按部就班的生活,可他却成了一个“双面人”; 《左撇子女人》里的女人有些不可思议,她毫无征兆地从看似和谐的婚姻关系中脱身而出。那些在寻常生活中微不足道的问题,却造就了他们的精神困局,晃动的钟摆突然失去了既定的节律,一切都被打乱了。
这样的变化之所以发生,最深层的原因来自他们对日常生活规定性的厌倦。拿科士尼格来说,他的工作就是每天打开法国的报纸,搜索“奥地利”和“奥地利人”这些字眼,以判断他的国家所具有的国际影响力。每一天坐在办公桌前,科士尼格手握一支油笔,在报纸上把关键字眼画出来,每半个小时起身收收传真,一天下来,他的手已经被报纸上的油墨染黑。他还要定期向法国媒体邮寄信件,以纠正报道中传统的奥地利的国家形象。从住所到办公室,日复一日,循环不已。
平心细想,每个人大概都有这样的时刻,只不过大多数人把厌倦当成对情绪的干扰而刻意躲避,作家却对此深究不放。彼得·汉德克让他的人物置身婚姻关系之中,通过这种最难处理和逃脱的关系来考验他们。当然,就深层意义而言,他们真正要处理的其实是自我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毫无例外地,身边的人都无法理解主人公们的真正想法,《左撇子女人》中的女人决绝地舍弃婚姻开始独立自主的生活,说不出任何正常的理由如对方外遇或者爱情不再什么的,这种行为因而显得格外怪异。她的丈夫以为这只是个心血来潮的玩笑,出版商以为舍弃婚姻的女人必然要寻找新的感情寄托。所有这些误解,无一不基于常识性的判断,认为女人为爱情和婚姻而存在,而其他价值不过是附属性的。可见人被模式化生活所塑造,又用这种模式来指导生活,让生活内容变得日益贫瘠。对于这些想要摆脱生活规定性的人物来说,他们不需要向外解释的理由,他们更想看清自己。也许他们并不知道确切的出路在哪里,但是知道想要摆脱什么,因此,他们总是在否定和放弃。
关键是找到安排“局限”的方式
如果因此认为彼得·汉德克只是借助小说来思考存在主题就未免简单化了。虽说他这个时期的作品被命名为“新主体性”小说,《短信长别》更是脱胎于他的真实经历,但是他深知自身经历或是虚构情节再曲折离奇,如果离开创造性的表达,也依然无法与旧有的方式有所不同,那样的作品必将失去应有的意义。所以,他以多样而独特的艺术手法,让小说文本显得复杂立体。在他的小说中,思考与叙述融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具体而言,最主要的特征就是让叙述紧紧跟随主人公的视角,沿着思绪纷乱的轨迹不断行进,这就使得叙述本身也变得矛盾和复杂。
以此观之,小说中各种看似复杂难解之处也就有了开启的按钮。比如那些不断叠加又逐渐放大的细节,它们与人物寻找和思考的进程紧密关联,它们被捡起,或被扔掉,总有一两个事物从中升起,成为启示性的路标。《短信长别》中女伴克莱尔的女儿对于安全感有一种病态的依赖,在她眼中所有的门都得关上,所有的纽扣都要扣好,否则她就会惊恐地大叫。孩子的各种反应触发了“我”的回忆,“我回忆起自己人生的第一件事就是我所发出的喊叫。当时,我被放在盆里洗澡,水塞突然一拔出,水从我下面汩汩地流出去。”这等琐事本来没有任何危险性,而人仍然会感到不安,也就是说危险常常会被夸大乃至虚构,安全感和模式化都是人面对不确定世界的工具,尽管它并不可靠。
假如小说在此结束,就会让那种缠绕不休的风格逊色不少,这时彼得·汉德克又将叙述拉回来。科士尼格不由自主地去叠孩子的白床单,把瘪掉的气球重新吹鼓,将掉在地上的书重又放回书架。秩序导致刻板,变化带来新奇,但反过来讲,失去秩序也可能带来混乱,变化的产生让人丧失安全感。所以,脱离既定轨迹后人又会通过再次建立秩序重新获得对事物的掌控,不管他们是否承认,最终他们还是要找到一个支点,以区分真实与虚幻,以确定他们的方向。他们终于明白“永远都不会摆脱掉所有这些局限,从现在起,关键是要为它们找到一种安排和生存方式,既适应于我,又让我在其中能够正确对待他人”。三部小说在结尾处都呈现出风暴过后的寂静状态:“我”在与妻子的一系列斗争中和平分手,科士尼格经历了妻离子散后依旧走在巴黎的街道上,女人送走了喧哗争吵的客人后独自开始画画儿,他们果真获得平静了吗?小说没有给出答案,但是我们可以预想到的是,只要生活存在,风暴仍将不止。
(原标题:寂静的“风暴眼”)

![8[0000-00-00 00:00:00]Š 8[0000-00-00 00:00:00]Š](/Upload/1488543337.jpg)
![导航上面VIP广告[2017-03-03 19:53:54]
导航上面VIP广告[2017-03-03 19:53:54]](/Upload/1491552790.gi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