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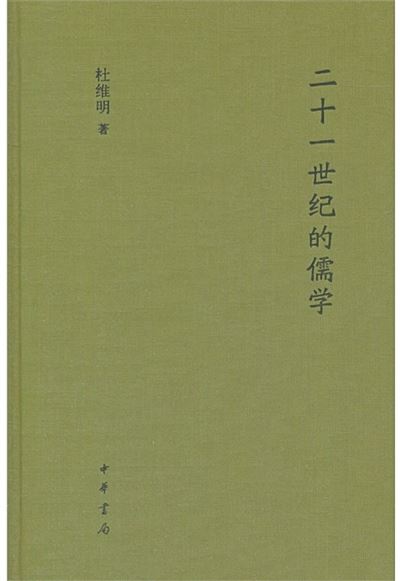 《二十一世纪的儒学》
《二十一世纪的儒学》
作者:杜维明
出版社:中华书局
2014年7月
定价:38.00
《二十一世纪的儒学》是新儒家代表人物杜维明的最新著作。作者在回顾了儒学的发展历程,反思了儒学在现代发展的困境和自我转化的基础上,提出了二十一世纪儒学的使命,对二十一世纪儒学面临的何为人、人生的意义、信仰等五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期待新儒学在二十一世纪为人们安身立命发挥更大作用。作者还结合他在国际上讲学、交流数十年的经验与体会,从多元化以及文明对话的角度解读儒家的内核精神及其在现代世界的命运。本报特邀北航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姚中秋撰文评述。
1
儒学是属于人的精神性普世之学
在新儒学大家中,杜维明的学思历程较为独特。
如先生所说,“1962年以来,我的学术生涯和英语世界密不可分”。几十年来,先生积极推动跨文明对话,以儒学基本理念与基督教、印度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展开对话。同时,先生对朝鲜、越南、日本乃至欧美新兴的儒学,也有涉猎。由此,“养成了从中国文化之外观察儒家的习惯,因此不接受儒家只是中国文化自我表述的观点”(第6页)。在这本书不算厚的文集中,先生论述了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儒学是真正属于人的精神性普世之学。
这听起来有点出人意料。因为,“普世”一词专属于地中海东岸兴起之神教:上帝是一,上帝对人的根本要求是信上帝,且毁弃所有其他神。故世界将定上帝这个一,上帝笼罩下的世界必定普遍同质,是所谓“普世”。
从文艺复兴时代起,人趋向开明,信仰松动,人文主义兴起。神本松动,人脱离神的管束,也就抛弃了一切超越。身体就是人的全部,人只有欲望,以及满足欲望之理智。按照《乐记》的说法,这个人文主义中的人已然“化物”,退化成物;或用胡兰成的话说,上帝照管下尚有神性希望的人,退化为高等动物。这样的人发明了另一套普适价值,并强势扩展。
按杜先生的说法,这是凡俗性人文主义。物化的人必定是个人主义的,也必定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只是满足其欲望的物的堆积而已。占有物,制造各种新奇的物,以满足无穷尽的欲望,这就是标准现代人的生命状态。从神本之“神明”,一转而为欲本之“物明”,但仍是普遍同质的:所有人都是一样的物化。
杜先生本乎儒家之学,提出“精神性人文主义”命题。杜先生早年诠释《中庸》,透过与神教的对比,已阐明儒家义理之这一特点。杜先生在哈佛上课,把韦伯引入美国学界的帕森斯说,基督教等宗教设定外在的绝对的神,引导人们超越世俗生活,转化世俗生活。儒家没有这样的神,故认同现实,接受现实,没有能力转化现实。杜先生对此表示异议,帕森斯乃修正其看法,但也只是说,儒家是要跟社会和谐的,与世俗之间没有那么大的张力。
2
在世俗生活中修行
对此,杜先生表示接受,但杜先生显然不会觉得足够。杜先生概括儒家核心义理是“内在超越”——不过,笔者不喜欢“超越”这个神教意味太浓的词,更喜欢说“人的自主提升”。天生人,赋人以仁之性,此性促人行动,发用内在之仁,首先是自修其身,然后由亲及疏,由近及远,如《中庸》所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也就是说,天地间万物皆为天所生,因而分有天之性。天不在世界之外,天就在世界中,世界之大全就是天。人在天所生之万物中,与万物自然一体,则仁民爱物,就是敬天事天。如杜先生所说:在儒家看来,“日常生活的世界有内在价值,我们不能抛弃掉日常生活去追求一个更高的真理。甚至可以说,最高的价值和意义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体现”(第84-85页)。在儒家看来,在日常生活中尽心、不违仁,则天下归于我之仁,同时成己成物,且赞天地之化育。
因此,儒家关注人,孔子说,士君子当致力于“为己之学”;但是,我只要对此自觉,即可自主提升,所谓“下学而上达”,上达于万物之本源——天。如果套用神教的说法,这就是“即凡入神”,日常生活就是道场,尽心生活就是修行。这就是人之“精神性”、或超越性维度。儒家以人为本,但人有天的引领,故不是物,而在世俗生活中有向上提升的精神追求。
这种精神性人文主义既非神本,又非人本,而在中道,人在大地上,在万物之中,但向天而生。这种精神性人文主义之核心价值是仁。仁是普适价值,而且具有最高普适程度。仁是切实的,仅就人而给人设定方向,每个人自己成为人,并把其他人当成与自己相同的人。仁又是高明的,成己成人成物而与上达于天。仁涵摄平等、自由、兼爱,而又可以避免光秃秃的平等、自由、兼爱必定造成的严重偏颇。
杜先生特别发明了仁、精神性人文主义对于文明、宗教之共存、对话的重大意义。
3
儒家不是宗教,是文教
杜先生反复阐明一个观点:每一种文明,每一种宗教,都应发展出两种意义世界,或者两套语言:一种是自己宗教传统中发展出来、面向自己信徒的特殊信仰语言,另一种是面对其他宗教及其信徒、面对其他文明的世界公民语言。
各种神教大体上只有面向自己信徒的特殊信仰语言。面向所有人的世界公民语言,在西方,只有凡俗性人文主义。但很显然,这种世界公民语言只能让世界败坏。
回望儒家,却别有洞天:儒家义理中本无特殊的信仰语言,而向来就是一套世界公民语言体系。这里涉及一个重大问题:儒家是不是宗教?杜先生认为,儒家具有宗教性,但不是宗教。我用了另外一个词来形容儒家之性质:文教。儒家不是宗教,而是文教。孔子以文教人,文就是道德,礼乐,以及各种各样的制度。文涵括了宗教,而且是各种宗教,让各种宗教相安无事。
儒家的这种性质、倾向给文明对话、沟通、协调提供了最好的观念基础。杜先生积极地推动文明对话,正是儒家精神之呈现。在这样的对话中,儒家没有神教的传教冲动,从不试图把自己的价值强加于人,而是希望与各家“和”,促成各家之“和”。仁的核心义理让儒家处理人际关系,邦国间关系,族群之间关系,宗教间关系,坚持一个原则:和而不同。
4
立足儒家,思考拯溺之道
再也没有比儒家宽容的了。西方普世价值如福山所说,让整个世界终结于同一个天国,不许另有想法。历史的终结意味着绝对的同一,各个族群、各个宗教、每个人被剥夺了选择的权利。仁才是宽和的、温情的普适价值,围绕这一价值展开的儒学是真正的普世之学。
二十一世纪的儒学当致力于普适仁之价值于全人类。对于儒学之现代发展的任务,牟宗三先生提出,当接纳民主、科学。此为牟先生孜孜以求者,而未免落于凡俗性人文主义的下乘。杜先生则以更为广阔的视野,提出儒学第三期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对西方文化的挑战做出创造性的回应。杜先生一直在做出回应,但更准确地说,杜先生一直在立足于儒家,给西方开药方,精神性人文主义就是儒家的药方。
杜先生树立了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典范。百年来,中国学人信心尽丧,在思想、学术上自甘为奴,包括新儒学的诸多努力,也只是身处绝境中的勉强防御而已,其论述模式不外乎:西方有的,儒家其实也有,只是不够充分,可在西方刺激发展。姿态如此卑下,其思考也就只是让儒家向西方靠拢,历史仍将终结于西方的宗教、价值、制度。儒家内在的伟大价值被取消了,中国之道终究要被抛弃。如此心态,儒学其实难说发展。
杜先生则转奴为主,立足于儒家,观世界之众生相,思考普遍的拯溺之道:见世人之迷于物,而提出精神性人文主义;见神教之过于执,而阐明和而不同之大义;最终确立仁为普适价值。儒家内在价值凸显出来,这价值是普遍的,不仅解决中国问题,更解决世界问题。有如此对世界敞开的天下情怀,儒家才有发展之契机,也才有存在之理由。
杜先生以自己深邃的思考、尤其是不懈的践履,勘定了世界意义上的儒学之大方向,接下来就看儒学者的思想创造力和儒者的实践智慧了。
□姚中秋
(原标题:儒家义理是一套世界公民语言体系)

![8[0000-00-00 00:00:00]Š 8[0000-00-00 00:00:00]Š](/Upload/1488543337.jpg)
![导航上面VIP广告[2017-03-03 19:53:54]
导航上面VIP广告[2017-03-03 19:53:54]](/Upload/1491552790.gif)

















